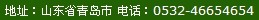|
如果严格地用文化词来说的话,我记忆里那朗朗上口的被我们农村的小屁孩称作顺口溜的小段子,是应该叫做童谣的。可至今我还是愿意叫它顺口溜,就像我把书本里叫做车前草的那种植物,在我们农村的土地上随处可见的那种不起眼的植物称为车轱辘菜一样,我觉得叫着随意,叫着亲切。最早记得的顺口溜,是奶奶哄我们的时候教给我们的,为了哄我们不哭,奶奶把我们放在大腿上颠,或是抱在怀里悠,再不就是用她的两个食指抵住我们的两个食指,跟我们玩对点游戏,天天重复,天长日久,自然也就记住了:“豆豆飞,豆豆飞,老爷儿(太阳)下山天就黑。豆豆飞,豆豆飞,丫头小子一大堆。”为了逗我们笑,奶奶常常坐在炕上,盘起腿,让我们用脚丫踹着她的膝盖,她和我们手拉手左右扯起来,一边扯手,一边有节奏地说着顺口溜:“扯大锯,拉大锯,姥姥门口唱大戏。接姑娘,叫女婿,小外甥,也要去。没啥吃,给她个羊粑粑蛋儿,”往往说到这里的时候,奶奶会抖一下我的下颌,随即做个往嘴里抿的动作,我就会咯咯地笑起来,去拨开奶奶的手,我可不想吃那肮脏的羊粑粑蛋。奶奶拽起因躲闪而躺在炕上的我,继续她的顺口溜:“羊粑粑蛋,架脚搓,搓碎了,打酒喝,喝多了,打老婆,打死老婆可怎么过。”说到这结束的时候,奶奶会抓住我,架着我的胳膊,用手或是伸过下巴咯吱我,我不掉泪她都不罢休。哄我弟弟的时候就换词了:“小小子,坐门墩,长大要不要媳妇,”然后让我弟弟说要,奶奶接着说:“要媳妇,干啥呀,点——灯,说——话儿,吹——灯,做——伴儿,一早晨,快起来,来给小小子梳小辫儿。”说得煞有介事,当“辫儿”的尾音结束的时候,就要去摸弟弟的后脑勺,弟弟当然也是跟我一样躲闪,奶奶也照样是像稀罕我一样地去收拾他。那时候小,就觉得奶奶的顺口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张口就来,“小耗子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吱吱吱,叫奶奶,奶奶说,该——”守着我姥姥,奶奶逗弄弟弟:“小崽崽,白眼球,你姥姥是个大马猴,小小子别发蒙,你姥姥是个老妖精。”当然姥姥也不示弱,回她道:“小小子,馋大年,你奶奶一会就屁弦。”那阵势,就像现在的陕北人对山歌,唱信天游一样,信手拈来,不加思索。等我走出奶奶的怀抱,跟大孩子们出去一帮一伙玩的时候,我可是眼界大开了,那些岁数比我大的孩子,玩游戏,都说顺口溜。玩干草垛游戏两伙人一唱一和:“干草垛,扔大刀,你的伙计记我挑。”,玩跳皮筋的时候那顺口溜就多了去了——“大白鸡,下白蛋,没有妈妈怎么办。跟狗睡,狗咬我,跟猫睡,猫挠我,爸爸送我托儿所;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儿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小皮球,架脚踢,马莲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三五六,三五七,三八三九四十一......九五六,九五七,九八九九一百一;小河流水哗啦啦,我和阿姨去偷瓜。阿姨偷俩我偷仨。阿姨跑了我挨抓,我妈说我大傻瓜;”偷瓜的那段顺口溜,有时为了好玩,常常把顺口溜里的“我”改成“你”,一帮孩子吵吵嚷嚷的,十分有趣。我们还玩编花篮,几个孩子每人一只脚着地,抬起来的腿交错着搭在一起围成一个圈,一边转圈跳,一边拍手说顺口溜:“编,编,编花篮儿,花篮里面有小孩儿。小孩小孩你别哭,过了腊八就杀猪,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小孩儿小孩儿你别哭,前面就是你大姑,你大姑,胖乎乎,原来是个老母猪;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爱吃萝卜爱吃菜,蹦蹦跳跳跑地快;小板凳四条腿,我给奶奶嗑瓜子,奶奶嫌我脏,我给奶奶下面汤,面汤有点稠,我给奶奶倒酱油,奶奶嫌我倒的多,我给奶奶砸了锅......”那时候的小孩子,记性真是好,听见外面树上喜鹊叫,也会冲着喜鹊嚷:“喜鹊喜鹊叫喳喳,你妈躺在树卡巴。拿刀来,嘎尾巴,拿盆来,接血啦。”奶奶说这样嚷几遍,那喳喳叫的喜鹊就会飞走的。猫头鹰给人的感觉就是恐惧,在我小时侯,夜猫子站在院里树上叫的时候经常有,每每听到猫头鹰叫,我就一遍又一遍背奶奶教给我的“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不是送喜,就是送财。”我们小时候有爱夜里哭的孩子,早晨起来经常会看见村子里谁家大门外的树上贴着一张黄色纸,纸上有用毛笔写的四行字,那时我们不认字却能熟背那上面的内容——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过路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我们小时候玩“木头人”游戏,游戏规则就是顺口溜,几个人一起拍着手蹦跳着说——大干瓢,破铜盆儿,我们都是木头人,一不许哭,二不许笑,三不许漏出大门牙,然后嘴巴紧绷起来,用肌肉、眼睛做各种挑逗的动作,谁要是忍不住笑了,谁就是输家;开春我们在墙角捉老道,拍着土,念经似的一遍遍重复:“老道老道往后少,老道老道往后少,”还真别说,那个灰不溜秋的小甲壳虫就真的慢慢往后倒;夏天在草叶上,树叶、菜叶上抓蜗牛,敲打着它的壳念叨:“水牛,水牛,先出犄角后出头;水牛,水牛,先出犄角后出头;”小孩子就是谁给了谁啥东西,或是许诺了什么,俩小指头一勾,都带着顺口溜的节奏说——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要(或不许变,就是不许反悔)。几个孩子一前一后走,也会有顺口溜——跟我学(xiáo),一嘴毛,跟我走,变花狗;雨天躲在门洞里看地上的水花,嘴也是不闲着——下雨了,冒泡儿了,老头戴上草帽儿了,要是看见有小伙伴带着米连头出来就立马改词:下雨了,冒泡儿了,王八戴上草帽儿了,于是一顿的唇枪舌战。小孩子在一起玩,红脸也快,和好也快,刚才还弄得面红耳赤,一会就拉起手对上顺口溜了:刮大风,下小雨,两个小孩卖苞米。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师找我爸,我爸打人可狠啦,啪,啪,打我两嘴巴,妈呀妈呀水开了,把我的脚丫烫歪了。扭一扭,瘸一瘸,过年穿不上大花鞋。提起过年,还有关于过年讨要压岁钱孩子给爷爷奶奶说的顺口溜:新年到,新年到,丫头要花,小子要炮,老头儿要顶新毡帽,老婆儿要要个新裹脚。冬天冷出不去的时候,小孩子们就在屋里围个圈玩“点三郎”,不论谁说这个顺口溜,都是从别人开始点“点一点二点三郎,三郎媳妇会打枪。枪对枪,杆对杆,不多不少十六个眼。”那个最后的字落到谁那,谁就另背一段顺口溜,当然也有挨罚学驴叫狗叫的。根据节奏,我悄悄发现,要想整谁很容易,点到的第四个人就是苦主,只要从想要整治的那个人倒着数回来,从一开始,那第四个人必定挨整无疑。后来上了学,在学校里学到的顺口溜就跟课本有联系了:大雨哗哗下,北京来电话,叫我去当兵,我还没长大;一年级的小豆包儿,一打一蹦高儿;三轮车,跑的快,上面坐个老太太,要五毛,给一块,你说奇怪不奇怪;我家小弟弟,梦中笑嘻嘻,问他笑什么,梦见毛主席;一朵红花红又红,刘胡兰姐姐是英雄,从小是个苦孩子,长大是个女英雄;咱俩好,咱俩好,咱俩上街买手表,你戴戴,我戴戴,你是地主的老太太;学习李向阳,坚决不投降,鬼子来抓我,我就跳大墙。大墙实在硬,我就钻地洞,地洞有枪子,专打小日本儿;xxxx年,我学会了开汽车,上坡——下坡,轧死二百多,警察来抓我,躲进女厕所,厕所没有灯,我掉进大粪坑,我和大粪做斗争,差点没牺牲,有人告诉了我爸爸,爸爸说我傻不愣登(更多的时候是把我改成你,逗趣);xxxx你想一想,你过去当过国民党,杀人家猪,宰人家养,抢人家十八岁的大姑娘;我有一个金娃娃,金胳膊金腿金头发。第一天,我到河边去打水,丢了我的金娃娃,我哭我哭我狠狠的哭;第二天我去河边去打水,找到了我的金娃娃,我笑我笑我狠狠的笑;第三天,日本鬼子来到我的家,抢了我的鸡,抢了我的鸭,抢走了我的金娃娃,最后给我俩耳瓜,我哭我哭我狠狠的哭;第四天解放军叔叔来到我的家,还了我的鸡,还了我的鸭,还了我的金娃娃,最后还给我一朵大红花,我笑我笑我狠狠的笑;手心手背,狼心狗肺,日本投降,中国万岁;xxx去赶集,买个辣椒当鸭梨,咬一口,齁辣滴,回去换个带把滴;拿同学打趣——你的脑袋像地球儿,有山有水有河流儿,有火车道,有火车头,还有三间大茅楼儿;在地上一个人玩画画也念念有词——一个丁老头,接我两个球,他说三天还,四天还没还,买了三根韭菜花了三毛三,买了四两肉,花了六毛六......不仅仅是听说来的,跟着学的,那时候我们都能自己顺着前一句的尾音自己编顺口溜了——你拍一我拍一,一个小孩开飞机;你拍二我拍二,两个小孩吃肉蛋儿,你拍三我拍三,三个小孩吃饼干,你拍四我拍四,四个小孩写大字......一直拍到是十。那天,洗完手,用毛巾擦手的时候,我无意中瞥见了自己手上那清晰的螺纹,久远的顺口溜立刻在脑海中闪念出来——一斗穷二斗富,三斗四斗卖豆腐,五斗六斗开当铺,七斗八斗把官做,九斗十斗享清福,呵呵,小时候的顺口溜,我竟然还记得这么清楚。童年就像一列远去的火车,在我生命的铁轨上已经远去,虽然远离了曾经远离了童年,可我悠远的回忆,鲜活的记忆还是那么清晰。想起童年,想起童年有趣的顺口溜,我的心中便没有了浮躁,没有了忧郁,没有了困惑,因为我又走进了那段无忧无虑的岁月。亲切的顺口溜,是我小时候那个年代不富有却无限充实的生活中的乐趣,是我童年里最简单的快乐,最质朴的纯真。 北票在线——北票人的网上家园! 订阅\\合作\\投稿①搜订阅号:beipiaozaixian②投稿信箱: qq.白癜风小偏方北京哪家医院治疗白癜风正规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chaoyangzx.com/cysrk/2782.html |
当前位置: 朝阳市 >那些丰富了我童年的顺口溜北票在线网
时间:2018/8/25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人成即佛成王凤仪言行录下一
- 下一篇文章: 警惕北票的朋友,诈骗新手法,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