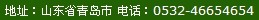|
从巴图营子受了4年再教育的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返城后会被分配到县袋白灰厂。在县砖厂礼堂公布后,像羔羊一样被赶上了“辽老大”,拉到了袋白灰厂,又被分到了北山场。走进山场一看,心顿时凉到了底:被削去了一半的大山,立陡立陡的,仿佛随时都有倾倒的可能。光着膀子人们在吃力地推着像小马车一样的大推车子。苍白又消瘦的脸上流淌着汗水,呆滞又冷漠的目光在诉说着无奈。没有通勤车,没有休息室,没有自来水,没有烧水蒸饭的地方。主任很爽快:工作是三班倒,每个人一个班推60车石头,石头块大的不能超过大饼子,小的不能小过鸡蛋。石头叫料,土和碎石叫渣,料里面不能有渣,清出来的渣,倒到渣道上去。你上老林那个班吧,明天正式上班。领完工作服,顺着骆驼营通往北票的铁道线往家走,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到四工村。第二天上班,全班13个人,一人一辆推车子,一人一把大板锹,一人一把大锤。一切都是陌生的,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主任或班长把他介绍给大家。他主动的和大家打招呼,人们带答不理,连看他的好眼神都没有,尽管是6月24日,尴尬的气氛让他感到了寒气的袭人。干活开始了,他们活干得非常快,用大板锹装石头,就像在装砂土,可他用大板锹怎么也铲不起石头;他们的大锤抡得上下翻飞,多大的石头都能砸开,他拿大锤砸石头就像在弹脑壳;他们推起车子就是跑,他推起车子步步艰难;他们干一阵子活坐下休息,蔑视地看着他,他找不到门道,越干越累。他偷偷地观察他们,感觉每个人的掌子面都比自己的好,而那工具更是有区别,尤其是林的那套家活式更好:推车子又窄又长,大板锹是一把削掉角的“跃马”牌钢锹,大锤安的是又光又亮的苦柳杆把。后来他才知道,只要是有新人来,就会给你一套破工具,然后大伙就铆足了劲快干,非得把新来的累吐血了才过瘾。自打上班后,林就开始调理他:换完工作服就叫他下山去蒸饭;吃饭时叫他下山去打水、取饭;休息时叫他去清理地沟、铁道;收工时叫他打扫掌子面。谁都可以指使他干这干那。他很来气,难道工人就这样吗!他又很不服气,我在巴图营子当了四年知青,啥活也没落在过别人的后头。他比别人早来,先准备好料,他看人家怎么铲石头时用力,抡大锤时怎样落锤,推车子怎样放,起步时怎样用力。尽管他的活干得快了,信心也足了,但仍没有改变大家对他的态度,尤其那个林,嘴里总是骂骂咧咧的,大伙也起着哄地调理他,仿佛只有调理他,才能解除身体的疲劳,才能感到心里的愉悦,而把他的大锤用渣埋起来,把他的推车子放汽,是人们每天必做的游戏。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屈辱,从未有过的孤单,从未有过的压抑。那天,当他正在装渣时,不知从哪儿飞来一锹土盖在他头上,在他揉眼的工夫,又有几锹沙土劈头盖脸地攘了过来。他强忍着怒火,艰难地推走了那车渣。等他返回再装渣的时候,方才还好好的锹把断了,在他愣神的工夫,林又骂开了:“你他妈的看啥,快点干,干不了说话!”随后是人们的哈哈大笑。他把车子一扔,走出了山场。林在后面喊:“你他妈的还走了,有能耐不干了!”坐在工棚里,感到很委屈,工作服脱到了一半又停了下来,一个月三十九元二的工资,对于因母亲有病拉了很多饥荒的家庭来说,是多么重要啊;这样回家怎么和父母说,两个弟弟又会怎么看这个当大哥的呢。理智又让他返回了山场。“你他妈的那个德行,有能耐走啊,熊种一个。”林更猖狂了,人们的嘲笑声更大了。刚刚还理智的他愤怒了:“你嘴干净点,我不是给你们家干呢!”林感到是在太岁的头上动了土,拎着大板锹就冲了过来:“你他妈的再说一句!”“说你咋地,惯的你。”还没等他话音落地,林的大板锹带着风声拍了过来。他急忙闪身,同时上步,立马放倒了林,林几次反扑,都被他放倒了。方才还幸灾乐祸的人们,才想起来拉仗。第二天,林没有来,记工员说请了事假。他霸占了林的那套家活式,一改蒸饭、打水的过去,常常用一种挑衅的目光窥视着大家。然而,他从前两天胜利者的滋滋喜悦中,渐渐地察觉到人们漂浮的眼神中暗藏着期待的目光,好像期待着一场暴风雨的来临。林是一个玩命的家伙,山场没人敢惹,而他也做好了恶战一场的准备,寂寞的人们在想象着这场战斗的惨烈。一周后,林上班了,似乎很淡定,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用起了他从前的破家活式,还破例地去蒸饭、打水。而站了上风的他,反倒不自在起来,第二天抢着蒸饭、打水,第三天,先进掌子用起了自己从前的家活式。袋白灰厂是一个月休息两天,当他休过两天上班时,发现自己的车子修理了,大铁板锹也换成了削了角的“跃马”钢锹。他没问是谁干的,人们也没有告诉他,但气氛经过这两天变得春暖花开了。林又是你他妈的、我他妈的了,他也融入了这个群体有说有笑的扯淡了。上三班(下午4点上班,半夜12点下班)休息时,林整来二斤猪头肉,一塑料桶散酒,请了大家。他纳闷,林这是抽的什么疯。林很坦然,但嘴还是不秃:“他妈的前阵子窑台的二驴子给我整了个人,北边的,我以为还是他妈来扯淡的,没想到那个娘们要和我来真的,相中我这白白净净的一米八大个了。小样的,会说话,着人疼,哥们心里放不下她了。往后不扯淡了,省着半夜回家连个捂被窝的都没有。”林这东西,说起了人话,原来这是女人的力量;他没来报复自己,也许与见了那个女人有关。女人啊,就是能耐,多么桀骜不驯的男人,都能给摆弄得服服帖帖的。他和那些兄弟们听得眼睛都直了,嗓子都干了,心里都长草了,都盼着找个北边的来温暖温暖自己那颗冰冷的心。说起了北边的,大家七嘴八舌地说开了:把握吗?别他妈的跟南边的那个似的。林激动了,“南边的那个娘们,把我这几年攒的钱都他妈的拐走了,逮住她,非扒了她不可!”说道伤心处,引起了共鸣:咱们是他妈的啥工人,就是他妈的两条腿的驴,这是他妈的人干的活吗!这白灰厂,除了出石头,就是他妈的出光棍。厂里的女工都不在厂里找对象,街里的、骆驼营的看不起咱们,连黄花营子的社员都不搭理咱们。起石头的,烧窑的,有几个人的娘们不是从大南边、大北边找来的。他听到这些苦衷,才领悟出在这大山上的人们为啥这么冷漠。也就在此时,工作失意的心头上,又蒙上了一层难搞对象的阴影。林是一个有心计的家伙,见把大伙的情绪勾起来了,便眼含热泪地说:“二驴子说,相完了门户,就该送彩礼了,最少元,叫六六大顺。我他妈的钱紧,看来这事要他妈的完犊子了。天下工友心连心,穷不帮穷谁照应,此时的他来了一身豪气:“林,还差多些,说话,北边的那个娘们一定给她拿下。”“拿下!拿下!”潮小伙子们、傻老爷们脸红脖子粗的喊完之后,把茶缸子里、饭盒盖里的酒碰了一下都干了。最后商定,打个会,后天开资,每人拿出30元,叫林先使。从此后,这十几个苦命人便像亲兄弟一样,都你他妈的、我他妈的不隔心了。人们说:其实林并不坏,就这这么个人,在山场干好几年了,眼看都三十,还没说上个人。进山场就有山场的规矩,都是从当孙子做起,都要先请上大家吃上两顿,买点烟酒啥的,这叫打平和,咱们厂子几十年的光荣传统,都让你小子给破坏了。这些天,他也感到那天的冲动是两把火烧的,一是对工作的万念俱灰,二才是林的臭毛病。那年的先进生产者是大家异口同声选的他。厂里的表彰大会准备得很丰盛,用袋白灰从巴图营子换来了小米,用汽车在下湾子帮工换来了猪肉。获奖者每人除得了一张没有镜框的奖状外,还有一碗小米饭和一碗红闷肉。他没舍得吃,打了两饭盒,上山和兄弟们解馋了。一个家住骆驼营却在市区上班的傻小子,找到政工股,要找人对换工作,说他大舅、他二舅都是铁路管车皮的,到这儿来就是开汽车的。他在政工股工作的同学早就想帮助他呢,几天的工夫就帮他办好了对调的手续。走的那天是二班(早8点上班,晚4点下班),纠结了一天的他,还是没有勇气与兄弟们告别。下班后他是最后一个走的,把那双套有新毡袜的靴子和那个大茶缸子放到了林的小箱子里(每人一个装过炸药的小木箱子)。也许是呼啸的北风刺痛了他的双眼,也许是山场的放炮声叫停了他的脚步,他站在骆驼营的大桥上,回首仰望着暮色苍茫北山场,竟然掉了几滴眼泪。哎,这小子多能装。许多年后,他听说,北边的那个也逗了林,林一气病倒后,再也没起来;还有两个也有病去世了;剩下的那几个在厂子黄了之后,到大南边、大北边跟着老婆种地去了。年9月8日中秋节本文作者为北票在线网友川州一夫,图片来自网络。点击下面“阅读原文”可查看文章原帖及网友留言。 北票在线: 电脑PC端网址:北京专业白癜风医院中科白癜风医院怎么样
|
当前位置: 朝阳市 >袋白灰厂的哥们北票在线网友川州一夫
时间:2018/8/23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多图朝阳全方位做好两会安保,南
- 下一篇文章: 北票一个女人和几百块一月的男人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