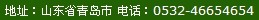|
中科白癜风医院善行天下 http://m.39.net/disease/a_6169059.html 孤竹风 作者:肖童 长河滚滚,大浪淘沙。 滦河以她堆叠如玉的浪花,冲刷着历史,荡涤着尘埃,曾经在滦河两岸指点江山、笑傲江湖的贤士仁人、英雄俊杰们,早已化做草原风、燕山骨、长城魂,成为草原牧民和长城子民们口中绵延不绝的传说。 滦河的东部,今天的卢龙、滦县、迁安、迁西等地,曾经成为一个古国的中心,这个古国早已淹没在历史的烟尘中,如今的人们,只能从发黄的史书中去寻找她的称谓:孤竹国。 熟知孤竹国的人不多,但孤竹国的两位王子却一直为后人所景仰和传颂。 三千年来,他们一直是“礼让”和“气节”的代名词。 孔子称他们是“古之贤人”。 司马迁更在《史记》中把他们列入70列传之首。 他们的名字叫伯夷和叔齐。 孤竹国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古国,做为商周时期的一个方国,它跟随商周的脚步,传国千年。但是,由于孤竹国地处蛮荒,远离中原,所以,在后来繁茂的中原文化这棵大树上,很难寻觅到“孤竹”的枝叶。孤竹国,就像西天大漠中的“楼兰古国”一样,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遐想。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从一些古籍中一探孤竹国的真容。并且,后来滦河流域的考古发现,又把孤竹国从古代的历史迷雾中推到了人们的近前。 孤竹,也作“觚竹”,意思是上古偏远的地方。《尔雅》中称:“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公元前16世纪商朝建立后,一些部落和部落联盟转变为商朝的"方国"。孤竹国是商朝在北方滦河流域的一个方国,国君复姓"墨胎"。墨胎氏在古籍中或作墨夷氏、目夷氏。《史纪-殷本纪》中说:"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可见,孤竹国国君是建立商王朝的商部落首领契的后代。 在19世纪初发现的甲骨文中,就有"孤竹"二字。年,辽宁省喀喇沁左旗蒙古族自治县出土的商代晚期铜罍上也铸有"孤竹"铭文。 综合《括地志》和《汉书。地理志》等古籍,我们可以知道孤竹国的缰域大致是这样的:北起辽宁省朝阳地区,南到渤海,西自滦河中游,东达大凌河。 关于孤竹国的都城所在,历来众说纷纭。目前比较公认的说法是:孤竹城位于滦县、卢龙、迁安三县交界处。 近些年来,在孤竹国的疆域内,除了辽宁省喀喇沁左旗的商代铜罍外,还发现了其它一批珍贵的商代铜器:有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克什克腾旗的商代前期铜器弦纹甗,有辽宁省朝阳市的商代中期铜器弦纹鼎,有河北省卢龙县的商代晚期铜器饕餮纹鼎和乳钉纹簋…… 发现,一个接着一个,一个又一个的发现告诉我们:孤竹国在商朝曾经兴盛一时,做为商朝的一个方国,它占据滦河流域,为促进华夏民族和北方夷族的融合做出了突出贡献。 孤竹国传国至商纣时期,国君名"初"字"子朝",人称其为"孤竹君"。孤竹君膝下有三子:长子伯夷,名"允"字"公信";次子佚名,已不可考;少子即"叔齐",名"致"字"公达"。伯夷、叔齐并不是他们的名字,而是"谥号"。 历史上著名的"夷齐让国"的佳话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司马迁《史纪》中的"伯夷列传"对此有详细的记载。 伯夷、叔齐是两位贤人。孤竹君生前留下遗命:传位于少子叔齐。孤竹君死后,叔齐认为长幼有序,不肯为君,遂让位于伯夷。但伯夷却说,传位叔齐是父王的遗命,怎能违背?也不肯做国君。推让不下,二人俱生离国之念。伯夷想:我在国中,弟弟必不安心继位,长此以往,于国不利。而叔齐也在想:传位于我是父亲的遗命,我若留在孤竹,让位于兄长,兄长必不接受,不如让国别走。就这样,伯夷、叔齐双双离开了孤竹。孤竹国的臣民只好拥戴孤竹君的次子为国君。 伯夷、叔齐离开孤竹后,闻听西歧周族在文王的治理下,内修仁政,尊贤敬老。决定到那里去看看。不想来到西歧后,文王已故,武王继位。在亚父姜尚的辅佐下,武王准备出兵讨伐商纣。而伯夷、叔齐认为:商纣虽然暴虐,但毕竟是天下共主,武王讨伐商纣是以下犯上、以臣犯君的大逆不道之事。再者,文王丧期未过,此时大动干戈,显然不合礼法。于是,当武王"牧誓"之时,伯夷、叔齐拦住武王的车马,谏诤说:"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武王的左右要杀掉他们,被姜尚拦住,姜尚说,伯夷、叔齐是仁义之人,扶他们走吧。 商纣灭亡后,天下并归周朝。时刻谨记自己为商朝臣子的伯夷、叔齐不愿侍周,逃到首阳山中隐居起来,并发誓不食周粟。就在二人采薇度日,行将饿死之时,一位妇人遇见了他们。妇人嗔怪道,你们真是迂腐之人,如今已是周朝的天下,别说是人,就连山石草木也都尽属武王了,你们发誓不食周粟,却采周朝的野菜,这不是很可笑的事吗? 妇人的一番话,让伯夷、叔齐如醍醐灌顶。到了这个时候,他们才意识到,天下虽大,却已是没有自己真正的容身之地了。二人哀叹道:"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吁嗟徂兮,命之危矣。"不久,伯夷、叔齐双双饿死在首阳山上。 伯夷、叔齐"让国相去、叩马谏伐、首阳采薇"的故事,自此广布人间,引来万世敬仰。 如今,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着一幅千年名画《采薇图》,作者是南宋大画家李唐。这幅画描绘了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首阳采薇"的故事。画面正中伯夷双手拢膝,倚树而坐,目光坚毅,神态自然;叔齐则左手撑地,倾身近于匍匐,右手指向兄长,言语着什么。二人虽然发蓬须长、面呈菜色,但是形散神不散,体弱气不衰。 打开这幅《采薇图》,相信每个人的心灵都会深感震颤、备受洗礼。那种发人深省、撼人心魄的感觉,穿越三千年的时空,直击我们的神经,在我们的心间回荡,在我们的脑中飞旋。 画面上,元代宋杞、明代祝允文、项允涉,清代翁方纲、蔡之定、林则徐、吴荣光等名人题跋留下的近百枚鉴赏印章,又仿如一段段精僻的论述,赞美着永不湮灭的"夷齐之风"。 在民间,尧舜禹时期是老百姓心目中理想的令人神往的大同社会。人人平等、个个向善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但是,在尧舜禹之后,从夏启建立夏朝开始,"世袭"便代替了"禅让",父子相传、兄弟相残成为每一个王朝的"秘史"。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伯夷、叔齐面对国君之位,竟然能够效法尧舜,让国别走,知耻自爱,沽守名节,实在难能可贵。虽然有人认为伯夷、叔齐后来的"不食周粟"未免有些迂腐,但他们"耻于争权夺利、乐于舍生取义"的精神却一直为后人所敬仰。 被尊称为"衍圣公"的孔子不仅称伯夷、叔齐为"古之贤人",而且赞颂他们"求仁得仁、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孟子也赞道:"伯夷,圣之清者也。""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 法家学说创始人韩非子则把伯夷与尧舜共称为"圣人",颂之曰:"圣人德若尧舜,行若伯夷。" 而作为孤竹后裔的墨子,更尊伯夷、叔齐为"宗圣",并以伯夷、叔齐为典范,传播墨家学说。 就连那位崇尚无为、酷喜逍遥的庄子,也对伯夷、叔齐备加推崇,赞叹道:"若伯夷、叔齐者,其于富贵也,苟不得已,则必不赖。高节戾行,独乐其志,不事于世,此二士之节也。"美誉伯夷、叔齐之高风亮节,行为脱俗,富有节操。 当中国进入漫长的封建社会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正统,被统治阶级视为"精神圣经"。儒家思想的核心便是"礼让"和"气节",而这,是被伯夷、叔齐很早就实践了的。 循着伯夷、叔齐在首阳山上踏出的足迹,一个个古代名士逶迤而来。夕阳如血,映红了他们飘忽的长衣,拉长了他们瘦长的身影…… 屈原,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当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能实现时,当目睹黑暗的现实而无力回天时,像伯夷、叔齐那样,他选择了死亡。清瘦的三闾大夫把自己沉入了汩罗江,实现了他"行比伯夷,置以为徐兮"的愿望。 司马迁,以一部无韵之离骚传史于后人,这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史学大家,在《史记》中讲述夷齐故事的时候,更多的是融入了切身的感受。毕竟,从司马迁的身上,你可以看到伯夷、叔齐的性格。 陶渊明,这位以构筑"桃花源"闻名于世的晋代大诗人,"夷齐之风"已经成为陶渊明的精神寄托。 唐代中期,朝庭内部矛盾重重,地方藩镇割据作乱,士大夫明哲保身,精神萎顿,盛唐士人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早已荡然无存。面对颓废的世风,著名文学大家韩愈特别撰写了一篇《伯夷颂》,称赞伯夷"信道笃而自知明"的精神和"不顾人之是非"的特立独行的风格,并感叹道:"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崒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 北宋政治家司马光有感于伯夷、叔齐的礼义和气节,曾经来到孤竹国旧地,游历位于滦河岸边的夷齐庙,并在这里留下了一首题诗。诗道:"夷齐双骨已成灰,独有清名日日新,饿死沟中人不识,可怜今古几多人?" 南宋末年,那位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而备受后世敬仰的文天祥,在国家行将灭忘的时刻,仍以"夷齐之风"激励自己。当元人劝降文天祥道:"国已亡矣,杀身以尚,谁复书之?"时,这位文丞相慨然对曰:"商非不亡,夷齐自不食周粟,人臣自尽其心,岂论书与不书?"在囚室中,文天祥感伯夷、叔齐的舍生取义,作《和夷齐西山歌》。歌道:“小雅尽废兮,出车采薇矣。戎有中国兮,人类熄矣。明王不兴兮,吾谁与归矣。抱春秋以没世兮,甚矣吾衰矣。” 在中国历史上,伯夷、叔齐的确是两位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虽然他们的故事距离我们越来越远,但是他们对后人的影响却越来越大,他们不仅受到诸子百家的推崇,而且被众多贤人志士、英雄豪杰视为精神偶像。就连封建帝王们也对他们频频施以礼遇。宋徽宗赵佶曾在年敕封伯夷、叔齐为"清惠侯"、"仁惠侯",元世祖忽必烈在年又特别"进侯加公",封伯夷、叔齐为"昭义清惠公"和"崇让仁惠公",年,明宪宗钦颁祭文,到了清朝,康熙、乾隆、嘉庆三位皇帝多次来到夷齐庙拜谒,留下御制诗文多篇。 夷齐庙就位于孤竹城的旧地,今天的滦县孙薛营村村北。夷齐庙的前身是建于年的"夷齐祠"。夷齐庙毁于"文革"期间,据老人们回忆,夷齐庙原是一座古城,北面以滦河岸边的陡峭石壁形成天然屏障,东、南、西三面筑有围墙,庙内正殿上供有伯夷、叔齐塑像,东西各有配殿,正殿的北面,在峭壁之上建有"清风台",许多文人骚客在这里留下了赞美伯夷、叔齐的诗文。 时间勿勿地来了,又勿勿地走了。 伯夷、叔齐的精神不灭,风范永存。 中华文明史中,将永远回响着一条河的声音。 "朝采山上薇,暮采山上薇。岁晏薇亦尽,饥来何所为?坐饮白石水,手把青松枝。击节独长歌,其声清且悲。枥马非不肥,所苦长絷维。豢豕非不饱,所忆意为牺。行行歌此曲,以慰常苦饥。" 你听,松林深处,一群孩子正在传诵白居易的那首古诗。 你看,滦河岸边,两位古人正在飘然向我们走来。 征稿启事——《栗花》面向全国及海外华人征稿。稿件范围:诗词,散文,小说,故事,文史,自传。所有稿件不限字数,可连载;投稿说明:本平台开通字以上原创稿件赞赏功能,赞赏金额全部返还作者,作为作者稿酬;投稿方式:加编辑
|
时间:2021/6/12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老太太骂那个人,可那人却病了老太的举动令
- 下一篇文章: 全国公示锡林浩特市上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