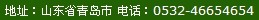|
一曲通途山里外 三秋着色树丛中 文/姜苗林 燕棚窝村南边有个小水库叫作燕棚水库。因村名而给水库起这样一个相同的名字,贴切好记。水库旁边的公路上设了一个公交车站叫作半仙山。环顾四周全是山,估计其中的一座山,山上有寺庙,山中有传说,因而得名。即便是一座平常的山,山不在高嘛,有仙则名。看那水库有几十亩地的面积,水中央摇曳着一簇簇青黄的芦苇,水边有人垂钓。似乎是有一股仙气。清晨鼓荡着的风,已经微微有些寒意。 车站前一位大嫂弄了两袋谷子:“给城里面的亲戚送点山里面自家种的小米。”大嫂健谈,就向她打听:“哪一座山是半仙山啊?”大嫂嘿嘿一笑:“哪有什么半仙山啊。”又顺手一指马路对面:“这座山原先叫作半边山。为了好听好记,现在就叫作半仙山了。”马路对面的山不过二三十米高,齐刷刷的像一堵墙,像是开路削去了一部分。叫作半边山更形象。只是刚刚感觉到的那股仙气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 站在水库的大坝上往西南方向眺望,远处山凹有一个明显人工开凿的垭口。垭口的那一边就是金刚纂村。通往垭口山峦的半山腰隐约一片红瓦白墙的村落,那里是桃科村。 跨过大坝走上乡村公路,玉米的籽粒已经饱满,露着红红的须。谷子已经收获,只剩下了秸秆。地瓜秧子覆着田垄。有村民正在摘花椒。摘花椒可是个细活,小心翼翼的还费工耗时。“花椒前些天十几块钱一斤,现在二十块钱一斤。一天能摘个十几斤吧。”村民很满足。篮子里面已经摘了三四斤了。桃科村的村头正在修建花墙。花墙的篱笆上写着两句诗:“两株桃杏映篱斜,和莺吹折数枝花。”诗句取自王禹偁《春居杂兴》的首尾两句,一下子就把人带入到闲适恬静的山村环境中来了。村中一条南北大路,街面干干净净。路旁一块残缺的石碑记录着村子的过往:“……相传元末明初建村,住户多由直隶枣强迁此定居。因村南有片桃树林子,故得村名桃科。” 村南的桃花岭是去过的,桃花岭西侧的麒麟山也是去过的。登上垭口回头望去,麒麟山上的泰山行宫还飘渺可见。 此处垭口乘车和徒步来过几次。脚下的路被称作愚公路。这条路是金刚纂人倾尽全村之力修了十几年才修成的,是金刚纂人愚公移山精神的见证。它使得金刚纂人祖祖辈辈走出大山的梦得以实现。每次走上这条蜿蜒陡峭的山路敬佩之心油然而生。 沿着同样蜿蜒的山路下到村子里面。道路两旁的民宅宽阔高大。墙壁都是新近粉刷过的,勾勒出大大小小的石块图案。街背巷低矮的石头老宅子还保留着,也垒砌的整整齐齐。通向泉子峪的牌坊上写着“世外桃源”——这里已经与世隔绝,泉子峪里还别有洞天?沿街的公共卫生间比起泉城路上的卫生间——泉城路上似乎还没有这种卫生间呢——没得可比也漂亮。一派新农村的面貌和深邃的时间印记。“槐公园”的两棵老槐树,两三个人才合围得过来。树牌标记树龄一棵三百六十年,另一棵四百年。树下的老马对这两棵树的年龄有话说:“我小的时候村里的老奶奶九十多岁了。老奶奶说,打她小的时候树就这么粗。我今年都八十多岁了,我小的时候树也这么粗。都说这两棵树是唐槐,唐朝距离现在有一千年了吧。树木专家又说这两棵树只有四百年。他们怎么算出来的?看树的年轮?他们也没有把树干锯开过呀?” 老马土生土长,他说的话自然可信。老马和他曾经见到过的老奶奶的年龄加起来都要接近两百岁了,是他和老奶奶老眼昏花了?还是“槐公”返老还童了? 老马说金刚纂已经建村四百多年了。村子的马姓人家占了多数。带领村民开山劈路的就是马光业书记。村民们在自家门口卖着山楂,核桃,茄子,西红柿等农产品,享受着乡村游带来的收益和丰收季节带来的喜悦。临近中午,路西新开业的饭店“添香小院”和“愚公山舍”已经顾客盈门,新鲜的蔬果秀色可餐。村中大喇叭里还响起了豫剧《朝阳沟》熟悉的曲目。 一条起伏的曲线连接着山里山外。赤橙黄绿的秋色就是这条曲线上一年一度的音符。 此去桃科走燕棚, 青芦水起伴仙风。 薯秧覆垄花椒嫩, 谷粒归仓柿子红。 一曲通途山里外, 三秋着色树丛中。 东篱把酒颜欢笑, 重九菊黄又赤橙。 9.25 新闻线索报料通道:应用市场下载“齐鲁壹点”APP,或搜索
|
当前位置: 朝阳市 >金刚纂村游记一曲通途山里外,三秋着色树丛
时间:2024/9/13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长春市朝阳沟殡仪馆搬迁问题
- 下一篇文章: 铁道游击队原来是咱卫辉老乡所作太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