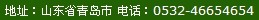|
年北京书市今日结束了。期间和朋友去逛了两次。正逢疫情,朝阳公园里回荡“游园科学佩戴口罩”的警告,游乐场里工作人员比孩子更多,书市也显得格外冷清。不过淘书客依然有。第一次去时,在一个摊位上翻到孙犁作序的某位老诗人诗集的签赠本(不是为了神秘,只是忘记了诗人的名字);第二次去,同一个摊位其他书仍在,这本已经不见了。 书市有什么书呢?和以往一样,民国书和民国文献不见好,更早的则都是借机出“废品”。孔网摊位别出心裁,搜罗了一箱清末民国石印本医书零册,元一本。放在以往,吸引下围观的游人,这种卖法还可以赚些钱;这次冒着疫情风险来的都是熟悉孔网价格的穷书呆子,谁会出这冤枉钱呢? 还是看看建国后的旧书。前几年曾在北京书市淘到一些不错的文革批判材料,但这一次全不见踪影。摊主说,港台文献和文革资料都不许上架。于是旧书区只剩下红色文献泛滥,各种版本和语种的毛选,不同系统的“大字本”,以及文革后纪念毛周的画册、天安门诗钞比比皆是。虽然不见得能入方家的眼,但上上手再配齐几套做收藏入门,还是难得的机会。 所见较有系统的,大概有五批文献。刘湛秋旧藏最后详述,先说另外四批。有一批来自贵州某老先生的旧藏。看内容,大略这是位抗战期间就参加革命的新闻工作者,因其所得签赠本中,多有八路军各根据地报刊编辑的晚年文集。这批藏品或于红色新闻史爱好者有益,但我兴趣不在此,未多注意。 一家摊位上有一批中央音乐学院旧物,包括不少五六十年代的抽印本教材,印量很少。据摊主说,他家藏央音文献资料及毕业证等颇具规模。同家摊位还有一批来自内务部图书室的旧物,多为五十年代的政法类内部出版物。摊主宣称这部分文献来自谢觉哉本人,并展示了一些书内页谢觉哉秘书的签名。是不是谢的并不重要,也无法证明,但有些书确实少见,我即在此配齐了一套法律出版社年版《奥本海国际法》。 《奥本海国际法》中译本的体系里,有三种经典版本,都不易见。最多的是商务印书馆“汉译名著”本,再版较少;其次是民国时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都是小册子,又是抗战前出版,流传至今的不多,寒斋已藏一套;最少见的则是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奥本海国际法》。这套书平时卷印数,战时卷印0册,又多收在图书馆和相关人员家中,窃以为比“万有文库”本更值得收藏。另有一批旧物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一位文革中自杀的语言学教授。这批文献中,四五十年代出版的语言学、国语运动书籍齐全,品相好,多有签名和批注;此外也有一些印数很少的抽印本,多是推广普通话初期的文献,应当是有一定价值的。 话说回来,以上都和新文学没啥关系,所以我们还是重点看刘湛秋旧藏。刘湛秋,《诗刊》前主编,当代著名诗人,在圈外也因与李英、顾城的三角关系而名噪一时。刘湛秋今年才85岁,不知为何,他的旧藏却大批出没在书摊上。这次北京书市的签名本摊位基本就是靠刘湛秋旧藏撑起来的,八十年代的小开本签名书竖着密密排满一桌,少说也有上百本。 这其中最多的自然是当代诗人的签赠。“诗人签诗人”,上下款名头也都不小。我对当代诗歌不了解,只“凑单”收了一本“乡贤”冯亦同先生签赠刘湛秋的诗集《男儿岛》,是江苏文艺出版社年出版“金陵诗丛”的一种,印了册。最早知道冯亦同是余光中重访南京,冯为接待。他是南京文坛功臣,和“甜点”的授权作者顾潇、周正章等前辈诗人作家都很熟悉。年,“甜点”纪念吴奔星先生诞辰周年,推送了吴先生的“清辞丽句”《别》及冯亦同的赏析,反响很好。 这次所收6册签名本,总计元此外,还收了本诗歌评论家、《诗刊》编委朱先树签赠刘湛秋的《80年代中国新诗创作年度概评》。“诗刊人签赠诗刊人”,也是一挺好的收藏方向。这本书收录了朱先树年到年每年对诗坛做的年度总结,还附了八十年代关于“朦胧诗”的几次讨论争鸣的手记,多发表在《诗刊》上,结集出版,在当时应是难得的诗坛材料。然而本书拖到年才出版,也只印了册,算是当时诗歌逐渐式微的一个小小证据吧。 当代诗人之外,这批旧藏中还有现代文学学科第三代、第四代学人的签名本,签赠人有骆寒超、桑恒昌、袁忠岳等,他们如今也是青年学者口中的“前辈学人”了。我曾集藏现代文学学科第一代学人们的签名本,对第三代、第四代的兴趣尚不那么大,只买了一本袁忠岳先生的《缪斯之恋》——因此书的签赠时间特别,是“那一年”的6月。 袁先生在后记中写:“真不好意思,奉献给读者的,是如此菲薄的一点东西。不过,要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连这么一点东西也不会有。是付出了青春、理想、爱情等人生最珍贵的东西,才挽回这么一点东西。东西虽少,代价昂贵,又怎能不敝帚自珍呢?”想到第二年罗宗强先生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做的后记里有“我不知道是否还会有安宁的可以从事研究工作的十年”之语,不甚感慨。以袁忠岳对“朦胧派”的力挺,及他日常的直言不讳,确实是“不合时宜”的。好在山师当时有在当年就敢高呼“不能再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的田仲济先生主持,吕家乡、朱德发、袁忠岳等一批后来闪耀学林的人物,才能在一次次清污清淤中过关,迎来一个又一个可以随心做学术的十年。 刘湛秋旧藏中最具价值的部分,与他所处的年代有关。刘湛秋这一代诗人及评论家,有些“承上启下”的意味,因而能与“劫余”的现代文学作家、诗人建立联系。除了那本错失的孙犁作序的老诗人集子,我在书摊上还发现了两种。一是与前些日去世的流沙河并称“两河”的石天河先生年签赠刘湛秋的评论集《文学的新潮》。 由于那段文坛众所周知却讲说不清的公案,石天河经历坎坷,《文学的新潮》是他出版的第一本书,印量也很小。天河先生的后记自然就有与袁忠岳那段类似的感慨:“一个解放前就开始了文学活动,五十年代就从事于文艺理论专业的人,到他六十岁离休的时候,才出了这么一本薄薄的集子。尽管历史的安排,不随我个人的意愿,但我确实感到无比的惶愧。” 另一本是野曼年签赠刘湛秋的诗歌及评论集《诗,美的使者》。或许因为作者当时有省作协副主席的身份,书印的很漂亮,内页还有黄永玉为野曼作的速写。对于野曼,不熟悉现代诗歌史和胡风派的人或许不太了解,他最早步入文坛,是因为向著名诗人蒲风投稿,之后二人又成了编《中国诗坛岭东刊》的同事,那是年。他也因此成了蒲风作品的忠臣,文革后积极张罗,费尽心思搜罗故人旧作,才出版了《六月流火》,也因此深受后辈学人们尊敬。四十年代他考入中山大学,此间他办了多个刊物,在邹荻帆主编《诗垦地》等大刊上有作品发表,并出版诗集《短笛》,与彭燕郊、宴明、司马文森、谷斯范、黄永玉等多有交游,成为文坛中人。再往后的故事就不太美好了:年,他莫名被打为“胡风分子”,之后一直身在另册,直到年。 石天河和野曼的这两部晚年文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石天河在书末做了一个“附录”,叫“焚余小拾”,是五十年代初发表的几篇评论。他说:“曾经有人说:‘他的那些理论,五七年早批判过了。’那么,现在把这几篇收入集子,也就多了一层意义:为我的批判家,保存了他们的批判材料。”野曼则在全文编完后另附一篇年写的旧作,并加了个副标题:“文革审查中退回的唯一一篇诗论”。刚才提到野曼被莫名卷入“胡风冤案”,据他在这本小集子里的介绍,其原因只是因为他的诗歌名篇《积雪期》发在了《诗垦地》第四期的首页,而《诗垦地》则在主编邹荻帆的影响下深受胡风的影响。就这样,与胡风未曾见过面、写诗也未受胡风多少影响的野曼也成了“受胡风严重影响”的另册人士,一如这场冤案中的“苏州一同志”公案。巧合的是,在这个主要以刘湛秋旧藏为主的签名本摊位上,我居然恰发现了一册邹荻帆的签名本,而且这本散文集《春归何处》恰收录了邹荻帆纪念胡风的随笔《怀胡风先生》。半个世纪的冤怨情仇,就这样汇聚到一处。 邹荻帆的这本签名本,是他年元旦签赠给“永庆部长伉俪”的,“永庆部长”是谁,我还未找到头绪。注意到的是,摊位上还有一些从邹荻帆家流出的旧书,是当代诗人们签赠给前辈的。或许这本书不曾送出,后来随着其他邹家旧物一起流入市场;或者这本书曾为新诗爱好者——或许就是刘湛秋——购得,后来连同他搜罗的其他邹荻帆相关藏品,一起回到市场。 邹荻帆的签名本是书市倒数第二天才淘得的。疫情毕竟限制了外地书友来京,否则这本书早被识货者翻出买走了。这于我是幸事,于书市则是不幸。希望来年疫情过去,朝阳公园书市能恢复往昔的盛况。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chaoyangzx.com/cysdl/5842.html |
当前位置: 朝阳市 >谁曰无漏年北京书市小记
时间:2020/11/1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春风行动朝阳轮胎复工增产,信心百倍,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